回顾||全球教席课堂89讲张永健:超越德国民法体系(Overcoming German Law)
2024年12月15日,雷火电竞官网在线全球教席学者、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Clarke讲席教授张永健以“超越德国民法体系(Overcoming German Law)”为题举办学术讲座。讲座由雷火电竞官网在线副院长戴昕主持,雷火电竞官网在线教授许德峰、长聘副教授纪海龙,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汪洋担任评议人。校内外多名师生参与其中,活动反响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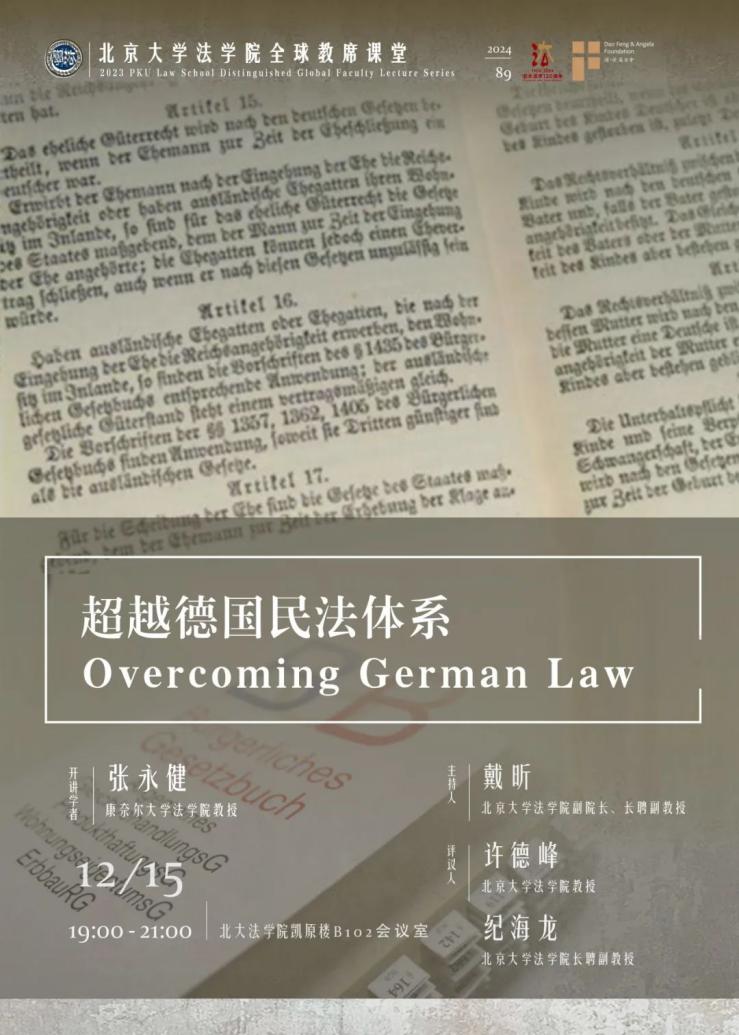
本文以文字实录的方式呈现讲座核心要点。

张永健:
从德国传来华人世界的民法理论的概念体系存在很多问题,它非常复杂,而且往往自相矛盾。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本土民法概念体系,而霍菲尔德的分析框架是一种可能的方法。因此我决定要写一本书,书名为《超越德国民法体系》,对民法体系进行重新解释。这本书所提出的概念体系与既有的德国民法体系是竞争的关系,但对民法体系的解释也并不限于这两种。霍菲尔德的分析框架是这本书会使用的分析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厘清一些概念。但因为其价值的中立性,并不会改变对价值的判断。
在霍菲尔德的框架中,所有民法上的法律关系都可以 化约成四组法律关系,分别是权利/请求权(right)—义务(duty),特权(privilege)—无权利/无请求权(no—right)、权力(power)—负担(liability)和豁免(immunity)—无能力(disability)。这四种简单关系的排列组合可以建构新的物权概念,并帮助我们理解既有德国民法体系存在的问题。比如德国民法体系认为,物权是对物的支配归属,但对于没有占有的抵押权人来说,应该无法实现对物的支配和归属。因而抵押权人不占有抵押物的情形和所有权人、用益物权人占有标的物的情形不应合并放在一起。德国民法还认为物权是人和物的关系,法律关系是民事主体间的关系,因而得出的推论是物权不是法律关系,债权物权化使得人和人的关系变为人和物的关系。另外,民法中的请求权、抗辩权、支配权和形成权这四项权利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同一个层次的权,传统观点对其共通性的解释“权利是一种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并没有提供额外有意义的信息。理论建构需要解决这些矛盾,要重新建构一个物上关系的理论,解释所有权人和第三人之间有什么样的霍菲尔德式法律关系。
根据霍菲尔德框架,物债二分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物权同时具备了合同、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这几种债权关系的共同特征,所有合同、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具备的特征,在物权法里也都有。因而,不存在物权和债权的确切二分。实际上,民法学内部的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不当得利法、人格权法各学科划分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形式。物债二分是一种只解决表象问题而未能涉及根本问题的“锯箭法”。
本书提出的理论建构为,民法和私法有三条轴线,我们掌握了这三条轴线,就可以把所有的私法法律关系放在这个三维空间之中。第一个轴线是法定不作为义务的义务人有多少。如果是传统的对世权,就表示事实上如果有n个人,就产生了n-1个法定不作为义务,即全世界所有的其他人都产生一个义务,例如不可以侵夺、占有、不可干扰物的使用等;另外一端是没有任何人有法定的不作为义务。按照这一理论,如果承认第三人侵害债权,则合同就具有一定的对世性,位于这一坐标轴的右侧;反之,如果不承认第三人侵害债权,即不应该让任何第三人在任何情况下承担侵害债权的责任,则合同位于对人的端点。第二条轴线衡量不同的排他程度以及它们对应的条件。第三条轴线是区分法律关系的中介。
使用这一理论分析常见的法律关系,可以发现人格权和物权其实都是在前两个轴线的右上角,它对世地对n-1个人产生拘束力,且其排他性没有附带条件,比如人格权随人出生即拥有,所有其他人自然对你有不可以侵害生命身体的义务,没有任何条件和取得时效的问题;合同的位置取决于你是否承认积极性和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因观点的不同可能会归入在这个二度空间上不同的地方,但不管哪一种,在霍菲尔德的框架下,它都可以得到描述;租赁则是一个准物上关系,原因在于其可能是准对世的,即比对人多、比纯粹的对世少,也就是只有部分人有法定的不作为义务,取决于实定法上的规定如何,譬如说如果法律规定是恶意的,第三人就受拘束,那么可以认为因为善意人不受拘束,所以世界上只有部分的人有法律不作为义务。例如在《民法典》中,买卖不破租赁的条件是必须要承租人在住,而其他国家有些要求租赁合同必须要登记才能买卖不破租赁,有些则要求占有,还有些地方要求公证租赁合同。因此,租赁属于纯合同、纯粹的物上关系还是准物上关系,在于承租人可以对抗多少第三人。如果承租人不能对抗任何第三人,就是纯粹的合同;如果可以无条件对抗所有的第三人,则是物上关系;如果有条件或有期限地对抗部分或全部第三人,则属于准物上关系。

对于占有关系,中国民法典对于占有者的占有保护很宽泛,也有非常多国家的占有保护范围比较窄。一些国家规定占有返还请求权的义务人范围是全世界;另一些国家规定必须要暴力侵夺的时候才可以有占有返还请求权,智利等一些国家规定占有人必须要已经占有了一年零一天才可以行使占有。
对于信托,大陆法系国家在这一框架下可以不局限于普通法系“双重所有权”的思路理解信托。信托法让受益人可以在受托人违反信托本质而处分财产的时候,可以撤销违反信托本质的移转,这就不是创造一个请求权义务关系,而是创造了受益人与全世界其他人之间的一个请求权义务。总结而言,信托受益人有一种原生义务,这个原生义务是在委托人跟受益人成立信托法律关系的时候自动通过法律与全世界其他人之间产生的。
对于抵押,一些国家的民法典把抵押放入物权编,也有一些国家按照罗马法的传统放入合同编或债编,还有一些国家将不动产抵押和一些其他的担保制度单独成编。使用三个轴线进行分析,在对世性方面,在登记生效的国家,抵押一旦成立,就已经可以对抗世界上所有的其他人了;如果是登记对抗制,则是准物上关系,原因在于登记本身是一个条件而不是无条件对抗所有人。中国的不动产抵押就是登记生效制度,没有额外条件。同时,民法典的很多规定表明了抵押的排他性,例如在先成立的权利可以排除后面成立的权利的干涉。中介条件方面,抵押以物作为中介基本不存在争议。抵押的另一个特点追及性实际上在理论中是对世性和排他性本来就包含的性质而非独立的特征。只要满足对世性和排他性,自然就有追及性,只要不用单独作为。最后,抵押的从属性并不是抵押的本质特征,而是简化法律关系、避免策略行为的一个设计,在最高额抵押等情形中也没有那么强烈的从属性。因此,只要满足对世、排他和以物为中介三项条件,基本就属于物上关系,从属性不会影响到定性,甚至如民法典第407条等规定,抵押的从属性可以约定排除。
问答环节:

许德峰:
我认为,法律在总体上属于规范科学,我们在讨论各种应然事项时的分析经常建立在特定的前提上,建立在人类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要有的价值上。民法中的很多概念是构建一个框架而使用的技术性的编纂概念,可能模糊,但是大体上能够涵盖我们想描述的事项。民法学者的研究并不非常关心概念框架的建构。比如说判断优先购买权人和优先承租权人的关系时,我关注的是能不能对抗特定人,至于它属于债权还是属于物权,我觉得无所谓。因此,如果要评估新框架的学术贡献,要看框架是否真的简化了问题。然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文化性使得新的框架未必提出了既有研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也没有简化问题。

纪海龙:
这个基于霍菲尔德理论的分析框架完全值得用、应该用。虽然有时不必须,但将概念分解到最小单元永远是更有利于分析的。民法中物和债的概念实际上是历史流变的产物,或许有一系列需要修修补补的地方,但是只要是大致可以使用,其实并不需要把它们全都抛掉。然而,我们同时需要用更精细的分析框架去把它里边的一些或许不够好的地方提取出来,这也构成了学术增量,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法律继受国家来说。

汪洋:
我们为了认识系统,必须要体系,必须要适度地简单化,但是为了回应社会的复杂性,那么体系又必须要具备适度的复杂性。学者会把这个事情让给立法决断,立法决断会把这个事情让给历史经验。人类持续的文明历史都是一种经验历史,而不是一种真实历史。法学与之同理,是一种历史经验。但是之后的实践发展表明,物权法和债法之间产生了多元化的关联。物债二分很多时候是一种描述而不是建构意义上的。既有的霍菲尔德分析框架未能与现行法产生有益的、增进知识的结合。我特别期待张永健老师对霍菲尔德框架的研究能有让我在智识上特别有收获的成果。
张永健:
我认识的很多民法学者非常重视概念。虽然可能一些民法学者在论文中对概念的认识已经很先进了,但学生、法官、检察官通过教科书接触到的更多还是传统的概念。这些缺点或者是矛盾,当然不是我第一个指出来的。但是,在此之前没有看到有人用我这套方法尝试去解决这个矛盾。如果认为概念本身很重要,或者解决概念之间的矛盾很重要,这就体现了这个框架的学术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