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上午,雷火电竞官网在线全球教席学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法学教授、伯克利法律与技术中心创始人及联合主任Robert Merges以“知识产权与研究方法”为题举办学术讲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郝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舸,雷火电竞官网在线教授张平,长聘副教授杨明、戴昕参与讲座,讲座由雷火电竞官网在线助理教授边仁君主持。校内外近百名听众参与其中,享受了一场学术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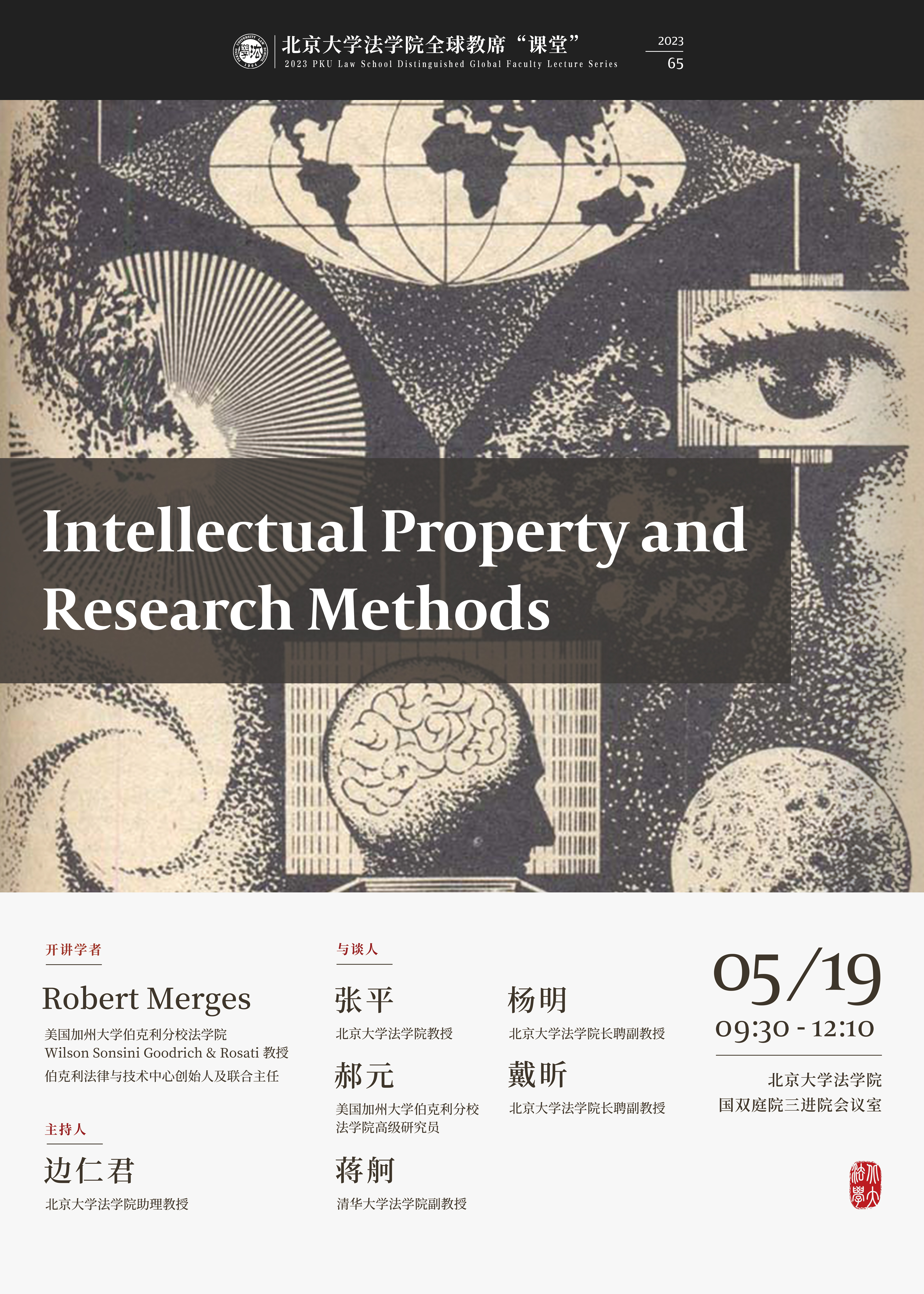
本文以文字实录的方式呈现讲座核心要点。
Robert Merges: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使用的研究方法曾发生过一些变化,但所有方法都是围绕着知识产权展开的。掌握一种研究方法意味着深入挖掘,真正从该方法的视角看待问题,这并非一日之功,而需要大量学习。在研究生时期,我主要学习了法律经济学。当我转变研究方法时,我几乎不可能在新的领域成为专家。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沉浸在文献之中,借助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找到正确的阅读材料。
法律经济学的兴起有其背景,那是对悠久的法学传统的一次“反叛”,不再将法律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年轻学者不要害怕“反叛”,那是获得动力的一种方式,就好像在蹬泳池壁。但是最近几年,我认为持续了上千年的法学传统可能比我所认为的更有价值,于是我决定回头来研究那些将法律视为一个自足系统的文献,尤其是私法文献。学术生涯如同一场马拉松,发表文章和取得教职都是持久战。
知识产权法通常是最先受到新技术冲击的领域,AI已经引起了专利申请的问题,用于训练的数据集也引发了版权问题。知识产权法的学子需要知道如何学习新技术,这也是一项特殊的技能。
传统方法不只是背诵案例和了解规则,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单个规则之上的推理和逻辑模式,学习规则运行的结构和互动的方式。一旦掌握了这些,你就拥有了一套“工具”,可以将它们应用于各种场景,包括新的技术和初学领域。
学者交流和学生提问:
一、 知识产权与传统方法:民法与比较法
张平:
我们曾经计划在雷火电竞官网在线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间开展一些合作,包括每年的技术论坛和大湾区的知识产权项目,二者均因疫情暂时耽延。我们将在不久的未来重启这些项目。
蒋舸:
我先讲述三个故事。其一,在德国,曾有人和我聊天,德语和法律德语是两门语言。其二,即使是德语为母语的人也很难读懂《德国民法典》的语句,19世纪的起草者就是采用了一种用词最少但理解最难的表达方式。其三,我的博导在攻读完纽约大学LL.M.学位回国后,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律文化冲击》(The Legal Culture Shock)的小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德国法律体系是一种“人造物”,人为程度极高。但当我阅读了很多德国哲学和文学后,我认为这是德意志传统所导致的自然结果。在现代德国形成之前,德意志饱经战争,现实世界令人感到痛苦,所以德意志哲学家们更想要使现实世界从属于观念世界。从康德开始,德意志传统认为观念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这深深影响了德国法律。其缺点在于,法律体系较为僵化,较难适应其他场景。其优点在于,法律体系较为容易理解和掌握,能够快速处理并应对问题。
Robert Merges:
如何用传统方法回答“AI是否可以成为作者”这一问题?
郝元:
在DABUS案中,世界各国的法院都采取传统的法解释方法,认为AI不能成为发明人,仅仅因为其并非人类。这个结论虽然有意义,但实际上是时候超越传统方法,从跨学科方法中吸取营养了。
AI相比于人类有一个缺陷,即它不能理解因果关系,强如Chat GPT也不能。但AI可以处理现实世界的技术挑战,将之拆解为一系列技术问题,这是人类才能做到的事。另外,Alpha Fold预测蛋白三维结构的准确率已经达到93%,非常接近实验结果。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人类与AI的协同。即使人类在提出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只要你对解决方案没有贡献,你就不是发明人。考虑到人类在协同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可能需要扩展发明人规则和创造性规则。
Robert Merges:
我认为可以总结为,发明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提出问题,法典要求有所冒险才能取得专利权,但新技术在这些问题上给我们带来新的洞察。新技术帮助我们理解基本原则,新问题促使我们反思基础问题。如果你能用不同方法得到相同的答案,你的答案就更加准确和坚实。
学生提问一:
对于年轻学者而言,未来想要成为了不起的知识产权学者,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Robert Merges:
我的答案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你真正关心什么?我在硅谷工作时,曾对科技的来由和激励方式产生了好奇心,这是我当年在软件行业工作的动力。软件为何不能取得专利权?这是否合理?我真正关心的是创新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学生提问二:
我们是否应该保护临床试验数据?是否应将临床试验数据的公开作为保护的前提条件?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
Robert Merges:
针对“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在传统框架下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从“物”和“财产”的概念出发。临床试验数据是记录在纸上的,纸张属于物。那么这里有没有超越纸张的物?你可以让概念由具体向抽象扩张,寻找“物”这一概念的极限。另一种是结果导向,考虑赋予财产权的结果如何。这不是一种经济方法,更应该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方法。这也是一种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传统。
针对其他两个问题,需要考虑这是否是一个类似于专利以公开换财产权的交易。我个人认为的确如此。因为保护临床试验数据的结果很像是财产权,那么对公开的要求也应该类似。但当深入到细节时,需要考虑到与财产权不同的问题,即侵权问题。全面公开让原告的律师可以获取所有的数据并借此提出指责。考虑对第三方的影响可能会改变答案,我认为结论可能是有限度的公开。
蒋舸:
针对“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当面对新问题时,我们会从既有的法律文本出发。但是既有的法律机器未必能给新问题提供可靠的方案。民法典颁布后,德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所以在德国,甚至是欧洲大陆,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得到接纳。
在中国,我建议首先寻找实质正确的答案,在此过程中可以使用实证数据。然后将答案并入既存的法律体系,以维持体系的稳定。但是对于问题本身而言,现实情况和实证数据更为重要。
二、知识产权与历史学
杨明:
我接触历史方法的原因,除了我对历史感兴趣外,是我认为历史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法律体系从何而来,我们又应如何将这套生态系统运用到现实案件中。人们在论证工业艺术体系的正当性时,通常将激励创新作为理论基础,但激励理论有其不合逻辑之处。为什么即使没有版权保护,创作也会繁荣?我认为历史能够做出解释,于是我翻译了《版权的起源》。该书讲解了版权体系如何产生,如何迎合市场需求以及如何促进版权贸易的产业化。
版权史可以带来三点启发。第一,市场是版权法的基础。第二,在理解作者和版权法的概念时,市场是重要因素。第三,对版权核心概念——独创性的理解至关重要。
Robert Merges:
几乎所有的教义学研究都带有历史色彩,但还是应该区分传统方法内的历史性工作和真正的历史方法。历史方法是作为外部文献让你审视问题。比如,专利的创造性要求从何而来?一种假设是,专利数量增加让法官感到专利审查不够严格。为了证明这一点,你需要考察专利诉讼的比例、授权专利的数量和经济发展的情况等。又如,版权法为何认为雇主是作者?运用传统方法,可以找到一系列历史上的案例。但若将历史作为外部信息来源,就可以找到一些内部视角找不到或者找不全的答案。
请问如何看待《窃书为雅罪》提出的观点?
郝元:
我认为该书很好地论述了其观点,但我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整体文化背景。
关于孔子,我想评论两点。其一,孔子是宋国贵族,拥有一些土地,但现在的创作者是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的。其二,孔子收束脩的方式是多元的,可以是钱,可以是其他物品。当下,版权恰好可以为创作者提供多元的选择,因为版权是一个权利束,你可以选择出售其中的一部分。但如果你没有版权,就什么都没有了。
蒋舸:
我认为法律是嵌入社会的一部分,受到社会运转的影响。我确实能够感受到一些传统统治方式仍存在于当今的法律中,但这并不明显。阅读中国历史让我感受到我们太多地将模糊的表述理解为道德表述。这可能是中国能够形成统一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很微弱和不准确,并且存在很多缺点。所以我们也会阅读李约瑟和黄仁宇的著作,来探究中国社会惯用的统治技巧,这也是知识产权历史的一部分。
Robert Merges:
该问题与发展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有关。4至6岁的孩子就可以将支配(control)与所有权(ownership)联系起来。他们也会认为在一个孩子的画作上标注另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不公平的。处于不同文化中的孩子之间有一些文化差异,但也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直觉,即拿走别人的功劳是错误的。因此,归属权(the right of attribution)不仅得到了经济学和道德的支持,也得到了发展心理学的支持。
学生提问三:
在版权史研究中,是否应该更多关注作者而非出版商?目前,部分作者的言论让我联想起中国的传统观念,如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如何证明历史的确在影响当下?一些中国古代的作者批评盗版破坏了其作品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种不带有经济考虑的想法是否意味着某种版权意识?
杨明:
首先,我认为不应该更多地关注作者。版权是市场的产物,作者和出版商都与市场相关,有时还与读者有关。法官需要决定如何在这些主体间分配利益。可能问题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出版商。针对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版权法的结构和基础从未根本性地改变过,版权法从一开始就遵循着相同的逻辑。问题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AI能否成为作者,而应在于版权法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们想用它保护什么。我认为作品的准确和完整在版权法中不太重要。它们可能与版权有关,但并不是版权法的重点。至于作者的观念,我们确实应该提升著作权法的立法,但立法不能完全被这些观念影响。我们还是应该看回市场,关注市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未来AI成为了真正的主体,我们就再也不需要著作权法了。
三、知识产权与经济学
戴昕:
在我的教学经验中,知识产权法的学生最容易接受法律经济学。即使在导论课程中,我讲授的并非知识产权问题,更多的是合同法问题,知识产权法的学生也很容易理解讲授内容,这与他们学习的知识产权法内容非常相关。
我认为经济分析就像一扇门,你可能不知道某种观点准确与否,但这种视角会引导你探索更深刻的问题。例如,有关最优的资源分配,一旦一个小公司拥有专利,它就有了更优势的市场地位,市场结构因此改变。虽然Merges教授提到了发展心理学的观点,但我认为在中国,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人造的政策产物,而不是一种自然权利。
关于交易成本,专利池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我们也会考虑垄断问题,如果我们阻止这种分配,分配效率就不会产生。不过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个经济理论框架,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领域,去分析问题是什么,需要怎样分析以及需要观察什么事实。在中国,我们仍然需要采用更好的方式搭建框架。至于实证分析,目前,我们对于交易成本话题所处的环境并不了解。至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专利池和交易成本问题,我认为只能通过对该产业的观察来解决。
学生提问四:
专利池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否还适用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应如何提升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专利池的表现?如何看待标准制定组织所带来的知识产权政策?
Robert Merges:
我认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标准必要专利问题中,最棘手的是汽车之间的协调问题。不同品牌的汽车应该可以互相对话,也都可以和控制系统对话;但各个品牌开发了自己的专有系统,并不想将其全部开放。问题集中在如何划分开放层和专有层,以及谁来制定开放交换标准。虽然目前是私主体在制定标准,但这是个政府层面的问题。你可以在理论上将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手机进行类比。首先,要划分开放层和专有层。其次,以制定标准的方式在开放部分的监管问题上达成一致。最后,给单独的技术组件定价。
四、知识产权与实证研究
Robert Merges:
中国知识产权普遍的侵权率如何?
边仁君:
被卷入纠纷的专利大约有2%,而这和美国的相关数据是一样的。
Robert Merges:
两国潜在的侵权率有所不同?如果美国的侵权行为更多,但被起诉的数量相同。在最优威慑理论下,这恰恰是美国加大惩罚力度的理由。
边仁君:
我认为这要看具体情况,两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的原告都是大公司,可能是因为诉讼费用过于高昂;但中国的原告大多只是个人或小发明人。中国的侵权行为可能要多一些,但侵权人大多是小规模的仿制工厂;美国的大公司会更了解侵权的成本和收益,侵权行为大多是独立发明,也会存在一些投机侵权。
Robert Merges:
如果因为我们只能抓住少数坏人,就对他们施加很高的惩罚,欧洲大陆会为此震惊和愤怒。他们认为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不应将社会政策放在惩罚上,惩罚应该针对个人的行为而量身定制。我认为,当你在谈论最优威慑时,你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传统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框架。
请问,如何建立数据集?以及收集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有何区别?
边仁君:
我认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几乎不可能自己独立收集一手数据,因为那会花费很多时间。我在伯克利法学院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用它来请学生帮我整理数据。实证研究不仅仅指向案例,也可以通过调查访谈等方式进行,但每种方式都不那么容易。
时常发生的糟糕事情是,在你付出巨大的努力后,数据却并不支持你的假设。另一个障碍在于,很多人会认为以数据证明一个常识没有意义。目前中国的研究通常从哲学价值出发,运用逻辑来构建规则;但现实世界十分复杂,在构建规则之后,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其效果。
Robert Merges:
实证研究中最惊讶的发现是什么?
边仁君:
我做了一项关于增加损害赔偿是否会阻止侵权的研究,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损害赔偿增加,侵权率并没有降低。有趣的是,这个结果与犯罪研究非常一致,后者在实证方法上已经非常成熟。他们的结论是,严厉的惩罚并没有减少犯罪活动。
这是我用过的最复杂的模型,我之前的大多数文章只是数数字。有些人会说,数数字太简单了,并非实证研究,但是,这取决于实证研究的阶段和可供使用的数据量。Merges教授总是告诉我,在黑暗的地方,有一只眼睛的人就是国王。研究可能不完美,但如果本来没有数据,那么简单甚至不完整的数据也就很有价值了。
郝元: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法律更像科学还是更像工程?今天我得出了初步结论,也许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更像工程。首先,它是人造的,去回应特定问题。其次,它对现实世界有影响,有比科学更为直接的影响。最后,它不像科学那样通过实验证明或证伪,传统的法律研究和工程一样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运转,工程师们未必知道原因,但知道该怎么做。但15世纪的科学革命给工程带来了更多的灵感。现在我们不仅知道做法,还知道了为什么这种方法有效,而另一种方法无效。
这个初步结论可以帮助回答另一个困难的问题,即如何在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某种程度上,私法是自给自足的,是可预测和稳定的。但同时,我们可以从更多的基础领域中汲取灵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会有所改进,会适应新的挑战。这对于知识产权法尤其重要,因为知识产权法的目标是促进创新和创造性表达,因此它对技术变革特别敏感。
我们如何面对DABUS案的挑战,即人类通过提出问题对发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传统法律下,这是否构成发明行为?目前,大概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让AI成为发明人,这与知识产权法的既有框架出入太大。第二种是放弃专利制度,将一切归于公共领域,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价值很高的发明失去激励。而我的论文采取了第三种方法,我借用了Merges教授的“中层原则”,比如尊严原则和效率原则,试图以更温和的方法将提出正确问题的人纳入其中。为此我深入地研究了规则。不论运用跨学科方法解决一个法律问题多么有趣,都必须要研究规则。法律规则像是“剑”,跨学科的知识像是“气”,我们都需要以气御剑。我们处于一个很精彩的时代,希望我们可以享受研究。
学生提问五:
为何在美国,只有专利和商标案件中存在加重赔偿?为何加重赔偿的最高赔偿为三倍?加重赔偿的目的是什么?从实证的角度看,目的是否实现了?
边仁君:
关于从实证的角度审视加重赔偿或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我会选择从制度的目的出发,在法律实施后进行一些校正。这也取决于你是否认为加重赔偿是惩罚性的。如果你相信惩罚性,那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如果你认为加重赔偿只是因为部分侵权行为没有被发现,那我们可以调查有多少侵权行为被发现、被起诉和被执行。这个比例在美国应该很高。
